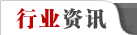加入WTO十年,中國農業的變化
《21世紀》:入世與中國的糧食市場開放,這兩者的關系如何理解?
鐘甫寧:上世紀70年代中期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出了一個糧食安全的定義,大意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能買得到也買得起維持積極生活和經濟活動所必需的足夠的食物。
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同時也進一步完善,加入了營養和品質安全方面的內容。無論如何,它關注的重點是消費者獲得充分食品的可能性是否有保障,至于這些食品的產地是本地、本國還是異國他鄉并不重要。
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人民福祉的角度看,如果目的是保障糧食安全而不是像日本那樣保證糧食生產者的收入,是否需要開放糧食市場不僅取決于中國能否生產滿足全國人民需要的足夠食物,而且取決于生產足夠食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和其它代價。
如果中國不僅能夠生產出足夠的食物,而且生產成本(價格)低于世界市場價格,無論是否開放糧食市場結果都一樣,中國不僅不會進口糧食,相反,可能還會出口剩余部分。
但是,如果中國無法生產出足夠的糧食,那么,進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們愿意回到通過發放糧票、油票和肉票等等來嚴格限制消費的年代。或者,中國雖然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但是,增加的成本可能很高,例如像日本那樣高出世界市場價4-5倍甚至更多,我們是否愿意為糧食及相關食品的消費支付如此高昂的價格?或者繳納同樣甚至更多的稅收以便經過政府補貼的轉移渠道維持低價?
同時還得意識到,增加糧食生產必然要爭奪本來用于其他商品生產的資源,其他商品的供應量也會減少,價格也會上升,生活水平和收入增長速度都將相應下降。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水平的40%,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水平的28%。如果缺乏某種資源,就應當通過貿易,用自己富裕資源所生產的產品交換自己稀缺資源所生產的產品。土地和淡水是中國的稀缺資源,就應當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交換土地和水資源密集型產品,包括糧食和其它一些農產品。否則,其代價必然是降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降低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增長速度。
我們曾經很自豪地宣稱中國用世界7%的耕地(實際大概是10%)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從為世界作貢獻的角度、為全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缺糧人口做貢獻的角度,我們確實可以引以為豪;但是,經濟上的代價和犧牲很大,過度使用邊際土地和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更加劇了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難度。如果有世界市場、全球資源可以利用,我們為什么要拒絕呢?
《21世紀》:入世后,中國糧食安全的話題一直被高度關注,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鐘甫寧:由于資源與人口的矛盾,非常有必要全面探討糧食安全的概念和相關政策。
首先,不能把糧食安全的概念簡單定義為一定比例的糧食自給率,更不能把糧食自給率當作一種政治口號甚至類似宗教信條一樣的東西,而應當把它和發展經濟、增加收入的目標放在一起通盤考慮。
如果把糧食自給率當做科學研究的對象,就應當全面考察實現的條件和手段:需要多少土地、淡水、化肥農藥和機械投入等等,必須考慮這些要素的可獲性和經濟成本。糧食禁運是主張保證糧食自給率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中國能源的外貿依存度更高,發生糧食禁運的時候是否同時也會面臨能源禁運?中國是否還能生產出必要數量的化肥農藥(即使不用考慮農業機械)?
其次,應當承認糧食安全是一個高度重要的概念,盡管不能機械地規定為一定比例的自給率,因而仍然需要討論如何加強食物供應的安全,包括數量和價格。
比較科學的做法是盡可能優化進口食物的種類和來源地。無論從政治還是心理因素考慮,如果需要大量進口食物,應當按照先油料、再飼料,最后口糧的順序;而這一順序恰好與我國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相符合:過去十多年有了的進口大幅度增長(其中也包括蛋白質飼料),近兩年飼料的進口開始增加,而口糧依然保持高度自給。因此,進口食物種類的問題無需特別關注。
為了提高糧食安全的保障程度,進口來源地應當盡量多元化。這一點在現實中也已經得到較好體現,比如大豆的進口總量中來自于美國和南美的差不多各占一半。進口來源地多元化的方針應當和農業國際合作的努力相結合。今后增加農業特別是糧食產量的最大潛力在南美、非洲和中亞。而這些地方擴大生產的潛力依賴于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農業生產技術的合作。如果我們通過對外合作的方式提高了這些地區的糧食生產潛力,就提高了全球的糧食供應,當然也提高了我國的糧食可獲性和糧食安全保障程度。
本文地址:http://www.qingqingav.com/industry/HTML/5026.html,如要轉載,請注明轉載自中國農業人才網